advertise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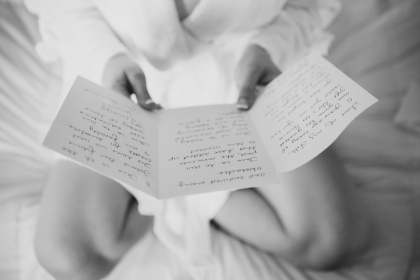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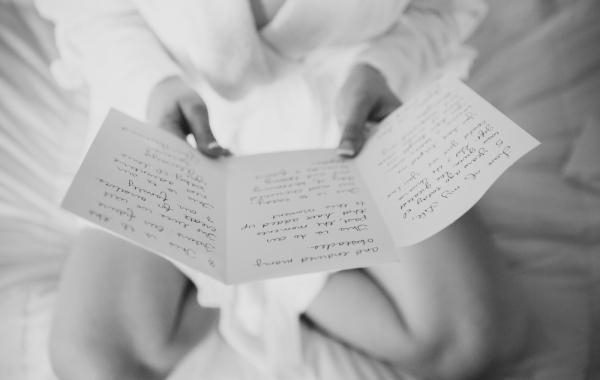
「我們分手吧!」
或許是街外的車聲掩蓋聲音,使聲音只有哀怨,而失去應有的力度。母親對老父的這句說話詐作充耳不聞,視線卻穿透了大木窗外,望向那幾盆大小不一的植物:鐵樹、百合竹、鵝掌藤······把整個露台都佈滿了生機。老父曾多次想在露台加上鐵窗,把它變成完整的室內,可是卻決絕地被母親阻止了。雖然這間房子算不上是我們的故居,但母親就是硬要保留一份西關小姐的優雅,說是懷緬外婆。在對街大廈還未變成全玻璃的冷酷建築物前的盛夏,她不時會走到露台,坐在那張老舊的藤椅上乘涼的。
「婉玲,這些年來······委屈了妳。」老父躺在床上,意識時好時壞,或許已忘記了我和弟弟的存在。在他還精神奕奕的時候,說話帶點鄉音,而且總是硬崩崩的。平常老父會叫母親做「孩子的媽」,只有他倆獨處的時候,才會罕有有展現出柔情的一面。
「委屈嗎?起初多少有一點,但也不算苦。」母親還是一貫說話的作風,很執著於用字。或許,這正是上一代知青的特色。
她在六十年代末跟老父結婚。那是一個瘋狂的年代,一個弱不禁風的女大學生竟然跑到農村跟一個小學也未畢業的農村男人結婚。幾年後,他倆逃難來港,接著就把我帶到這個世界。
「說起來,妳還記得第一次為我做飯嗎?」老父突然把話題轉變了。「很苦的。」
「幹嘛要記住!」母親沒有半點抗議,倒像是回味從前。
「因為妳是我人生唯一的美好記憶。」
「太肉麻了。」
母親的視線雖然由始至終沒有離開過窗外,但卻沒有半點不敬,因為老父的雙眼早已看不到了。這兩年,母親是他的眼睛。也難得母親來港後以寫作為主要收入,所以沒有刻板的指示式說話,例如「轉了紅燈,停下來吧」或「碗筷在這裡」之類。要是我活在黑暗之中仍要聽從指令的話,我的內心必定會比黑暗更黑,黑得如被埋在絕望的深土。她總是優雅地描述世界,例如「今日的陽光照到沙發的背了,摸一下吧!很暖的。」,又或是微笑著的、簡單的、意味深長的······
「樹葉變黃了。」
如果當日情竇初開的我沒有不知所措,也沒有壯著膽地向母親問她跟老父的情史的話,我還會一直被他倆虛偽的恩愛表現欺騙。女人的狡猾或許不是與身俱來,而是遺傳的。
母親欺騙了所有在香港新生活後認識的人,就連我這個親生女兒也不放過。她的書迷們都以為她的優雅來自良好的家庭及幸福的愛情。然而,他們並不明白女人總容易叫人相信刻意營造出來的誤會。我也是後來才知道那些書中美麗的愛情故事,是從外婆身上偷來的。當然,精明的老父大抵早就看穿母親的把戲,所以才跟她相見如賓吧!
「媽媽,我想知道妳為什麼跟爸爸結婚?」在我十六歲的某日,我趁老父還在上班時問母親。
那個時候,母親已有一點名氣,出了好幾本書。回歸前十年,在那條嗅到玫瑰花香的經濟公路上,只要懂包裝,沒有東西是賣不了,包括小說。現在看起來或許會有點不可思議,但那時單靠版稅就能供我們一家四口基本的生活了。原本可以輕鬆地過日子,可是偏執的老父卻堅持要到工廠上班。母親也無可奈何,就只好由他了。
「妳這棵十月芥菜,終於也問起這個來。喜歡上男孩了嗎?」
母親的心思就是如此細膩,不必照鏡子,我也知道自己的臉立即紅起來,一道火灼的熱力從胸口湧到頭頂。她倒是輕鬆得很,從房中拿出一已發黃的封信交到我手上。上面寫著幾個字,我認得是老父的筆跡。
「遺書?」我驚訝地問:「爸爸有病嗎?」
「還未有,我也是偶然發現的。」那個時候,老父仍健康得很。「男人總有些說話是恥於開口的,所以就把它當是我倆母女之間的秘密吧!看完後,妳就明白了。」
婉玲:
首先要跟妳說抱歉。請不要誤會,我並沒有跟其他女人做過什麼苟且的事。因為能跟妳一起,已經是我平凡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我要跟妳道歉,是因為這些年來,一直要妳委屈地跟我走在一起。請相信我,我是知道自己配不上妳的。
打從我們第一次見面開始,我的震撼已經不能言語。一隊大學生插隊來到農村下鄉幹粗活,這原本就是一件極度荒謬的事。但相比起來,妳在田野辛勞的身影更讓我迷醉。在陽光下,妳串串滴下的汗水閃出與眾不同的光芒。即使妳半點笑容也沒有,臉上也被泥巴弄髒,但妳的樣子還是深深吸引著我。
如今我不再隱瞞妳,就是我們的相親並不是完全被動的,我曾向公所的領導提出對妳的傾慕。聽說妳是自願參加下鄉活動。那個時候,像妳這種知青女生嫁到鄉下,也算得上時髦。可是,我並不了解妳的過去,也不知道原來妳來自廣州的書香之家。我只是膚淺地愛上妳,卻間接把妳推跌落痛苦深淵。
1969年,我們的新婚應該讓妳很失望吧!我從妳日後的小說中才知道原來女人一生也憧憬著浪漫,可是在那個艱難及荒誕的日子,我們的婚禮連半點色彩也沒有,只對像那張目無表情,卻又備受崇拜的主席忠字台前締結。鄉里也穿上清一色或是灰藍,或是深綠的衣服到賀。請妳原諒他們,跟妳成長的大城市不同,他們已穿上最好的衣服到來了,最少沒有破洞。
那個晚上,我還以為妳只因新婚而緊張過度,所以才目無表情。但當晚我們親熱······不!那只是我單方面的美好幻想,應該是在我冒犯妳之後,妳的淚水及飲泣訴說出妳內心的委屈。我在那個時候才明白結婚並沒有為妳帶來愛情。事實上,愛情應該是結婚的前提。在為國內走上什麼道路、建設不知所謂的社會主義新農村、還有不明不白的反修及防修······種種冠冕堂皇卻又虛無縹緲的讚頌中,妳對愛情的憧憬被我粗暴地踐踏;妳精緻的身體也被我無情地蹂躪。
那個年頭,瘋狂的人都無知地以為女人可以理想去換取愛情,我感到很厭惡。所以,即使父母在往後不停催促我們要生小孩,我也不敢再犯。我怕再一次擠出妳的眼淚。在妳之前,我沒有碰過其他女人。所以我不是妳口中的冷淡,也不是妳心中的冷靜,我只是不懂面對我倆的情感,而且也沒可傾談的對象。因為妳已成了村內的模範及人民的榜樣,一點點質疑也可能被當成修正主義者······哪怕只是我倆之間的事。因此,當我發現妳要逃到香港時,我真的義無反顧去支持妳。
「就算是粉身碎骨,我也要保護自己的愛人!」
或許我不配這樣豪情壯語,或許我說起來有點可笑,但在那個摸黑的晚上,我才第一次清晰地見到妳的笑容。所以在那一晚,我暗自發誓會為妳奮不顧身。幸運地,我們能在這個地方落地生根。
雖然我們並沒有如妳小說中激烈的戀情,但我相信在這個新地方,妳已找到妳追尋的自己及幸福。有人說妳現在的成就比我高太多,著我小心妳會離開。我反而奇怪,這不是理所當然的事嗎?而且,能一直保護妳來到這個新環境中盡展妳的才華,獲得他人的認同,已經是我一生最大成就。
我知道妳是一個傳統的女人,即使妳何等不願,但也克盡妻子的本份。因此,要是有一日我離開這個世界的話,請不必顧慮我,我已經佔據了妳太多了。放手找尋屬於妳的幸福吧!
夫 進程
1980年 枯葉落下時
看完整封信後,我呆呆地望著母親,實在想像不到他倆經歷過的時代。我終於明白老父的拘謹源於一份內疚,而這封信就是希望得到寬恕的工具。一直以來,他也是抱著這份沉重的心情,實在太可憐了。突然,我想到一個問題······
「信內說自從新婚當晚後,爸爸就······那我是妳親生的嗎?」
「當然啦!」母親意味深長地望出窗外。「沒有他,或許我一生也只好落田種菜。逃到香港的路徑,絕對稱得上兇險萬分。所以來到香港後,我採取了主動。幾年後,就生下了妳。」
那一刻,我意識到跟我傾訴的不是一位母親,而是作為女人之間的密話。這個女人也太厲害了,把愛與恨都淡淡地演繹了出來;看似已原諒了他的丈夫,但實際上又把他蒙在鼓裡。而且,她連自己也欺騙了。
「我們分手吧!」
「樹葉變黃了。」
這一生,你也不能離開我。


